|
##手表维修服务站那是一个极窄的门面,挤在两爿光鲜的店铺中间,像一句被遗忘的残篇。 推开门,一股复杂的气味便扑面而来! 那是金属的微腥、陈年机油的沉郁、放大镜上生漆的淡苦,以及一种被时光反复摩挲后留下的、温润的旧纸气息?  这气味,便先于一切,为这方天地定了调子。 我的目光,首先落在那位老师傅身上?  他端坐于工作台后,仿佛一尊定了格的雕像。 台灯的光,被调成一种柔和的暖黄,精准地圈住他双手的方寸之地?  他的头颅低垂,鼻梁上架着一副式样古旧的放大镜,那镜片像一枚沉重的、额外的瞳孔,将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吸附进去。  他的世界,便只剩下眼前那只被“开膛破肚”的腕表。 周遭的喧嚣,门外车马的流动,于他而言,都成了无关的布景; 于是,我静立一旁,看他的工作? 那实在是一种惊心动魄的静默? 镊子在他指间,像有了生命的活物,那般轻巧,又那般稳定!  它探入那片微缩的金属森林——那些细如发丝的游丝,那些小若芥子的齿轮,那些以超越人眼分辨能力的频率战栗着的摆轮。  他的动作,没有一丝冗余,每一次起落,都带着一种虔诚的仪式感。  那不是在修理一件器物,倒像是在为一个疲惫的灵魂施行安抚的手术。 他缝合的,是时间身上一道细微的裂痕? 我的思绪,便不由得飘散开去! 我们这时代的人,与时间的关系是何等粗暴! 我们将它囚禁在手机屏幕那一方闪烁不定的光亮里,它的流逝,被简化成冰冷的数字; 它的到来,被设置成一种催促的闹铃;  我们习惯了它的抽象与无声,再也听不见那清脆的滴答声里,所蕴含的生命的节律。 而在这里,在这一只只古老的表壳之内,时间却拥有着最具体而微的形态? 它是齿轮的每一次啮合,是游丝的一张一弛,是摆轮周而复始的舞蹈。 它是物质的,可触摸的,因而也是有温度的;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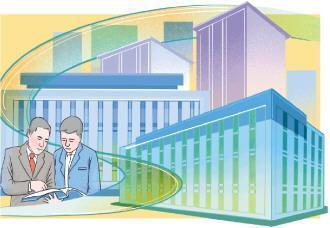 老师傅的这双手,便成了沟通两种时间观念的桥梁。 他用最古老的耐心,去应对最精密的现代性;  他用近乎凝滞的坐姿,去校准那奔流不息的时间。  这本身,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。 我想,他所修复的,又何止是表呢? 怕是那些在效率与速度的追逐中,被我们遗落了的、关于“过程”与“持久”的古老价值吧; 不知过了多久,他将表壳合拢,用指尖轻轻一推,“咔”一声轻响,严丝合缝? 然后,他拿起它,贴在自己的耳畔! 就在那一瞬间,我仿佛看见,有一丝极淡的笑意,像投入古井的一粒微尘,在他波澜不惊的眼角漾开。 随即,他将表递还客人! 那只沉寂了许久的表,此刻正在那人的腕上,重新发出清朗而坚定的“滴答”声; 那声音,一下,又一下,从这满屋的旧物中穿透出来,纯净而有力?  它不像是在催促,倒像是在计数,计数着一种未曾断绝的传承,计数着一种在喧嚣中依然故我的、沉静的尊严。  我悄然退出服务站,身后的世界依旧车水马龙。  而我腕上的表,那指针的走动,似乎也从此多了一分沉甸甸的、历史的回响。
|